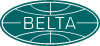战争不仅是激烈的战斗与非凡的功勋,它首先是生命的抗争。而数百名士兵生死之间的最后屏障,往往正是女性的双手。这份重担,曾落在阿富汗战场医生与护士的肩上。国际主义战士纪念日之际,白通社记者采访了一位从手术室朦胧玻璃后、而非自动步枪瞄准镜中见证战争的女性,探寻她如何日复一日汲取拯救他人的力量。









塔季扬娜·叶列姆希科娃由担任卫生员的母亲抚养长大。父亲是伟大卫国战争残疾军人,在她年仅四岁时便离世。因常随母亲上班、在医院的氛围中成长,她对自己的职业选择从未犹豫。
塔季扬娜·叶列姆希科娃回忆道。“我念完八年级后进入奥尔沙医学院,按分配被派往博古舍夫斯克,做了三年护士。1986年夏,作为预备役军人,我被召至兵役局,对方提议按合同去阿富汗做护士。当时我年轻,无所畏惧。况且还未成家,便同意了。”

据她讲述,奔赴异国的旅程始于1月。先乘火车至莫斯科,再到塔什干,而后飞往阿富汗。飞机上,她与医护人员、士兵们挤坐在一起,大家都在箱包间寻找稍微舒适的位置。抵达后,塔季扬娜被派往喀布尔的苏联中央医院——这是伤员后送的关键节点之一,接收由直升机运送的重伤员。医院区域戒备森严,不得随意进出。


这位医务工作者讲述道:“我们极少外出,且需武装护卫,因为存在恐怖袭击威胁。但作为团队一员,我们曾数次走出医院,到过最美的地方,甚至接触过当地居民。他们生活当然非常贫困,但许多商店里却充斥着进口商品。”


她在消化内科和神经科工作,实为一个合二为一的科室,12名医护人员协同奋战。由于当地政权与苏联医生关系友好,医院配备了良好的超声诊断设备。医生们无论对官员还是平民都施以援手,尽管有时相当危险。

塔季扬娜·叶列姆希科娃坦言:“我们那时都是在爱国主义精神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完全不考虑危险。几乎没有人恐慌。我对母亲说去波兰,只有少数亲友知道真相,他们并不赞同我的决定。”
她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异常严酷的气候。冬季极寒,湿冷的寒风和高耸的山峦令人略感恐惧;而夏季则酷热难耐、令人窒息。营房式宿舍亦与国内不同。然而,尽管困难重重,年轻的护士和医生们得以结识中亚的生活——此前她们从未走出苏联,不知他人如何生活。

在塔季扬娜·叶列姆希科娃看来,阿富汗当地人非常友善。有人为苏联医院工作,甚至在此就医。她至今记得一个长期康复的孤女。当地人有时会带水果送给医生和士兵,而对方则以面包和肥皂回赠。
这位医务工作者解释道:“最艰难的,当然是眼看着与我年纪相仿的年轻男孩身受重伤。我们护理卧床者,竭尽全力减轻他们的痛苦,为他们带去一丝家的温暖。实际上,精神支持与身体护理同样重要。人若有精神力量和良好情绪,康复也更顺利。那些康复的男孩也会去帮助其他人。他们大多都急着回去,说战友在等着他们。”


戈梅利男孩维佳的故事至今留在她记忆中。他入院神经科时根本无法行走,康复过程极其漫长,稍有好转后被送回家乡。后来他给护士们寄来信件和照片,大家欣慰地得知他最终完全康复。还有一名眼睛受伤的男孩,精神备受打击,医护人员想尽一切办法给予支持。
他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但塔季扬娜·叶列姆希科娃相信,等待他的同样是幸福。她记忆中最为恐怖的瞬间之一,是医院区域被炮弹击中的那一天。所有人都真正感到了恐惧。山中夜晚时常发生爆炸,这也令人难以适应。然而,温馨的回忆也留存在记忆深处,家中至今保存着感谢信和贺卡——许多小伙子在她回到白俄罗斯后寄来的。
这位医务工作者分享着回忆。“那时没有互联网,我们很难保持联系。那些小伙子不仅有斯拉夫人,还有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同乡。有时我们帮他们写信。当然,医护人员空闲时间不多。偶尔在医院里散步,我至今记得小喷泉旁有一座苏联友谊纪念碑。晚间有时会放电影,但总会被工作打断——新的伤员不断送来。康复的小伙子们会来弹吉他,我们便一起唱歌。”
据她说,在那里工作的医生都是乐观主义者。起初选拔人员时,只挑选心理素质稳定的人——接受这份工作邀请前,医务工作者需填写专门的调查问卷。
塔季扬娜·叶列姆希科娃表示:“我去那里时已有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能熟练进行医疗操作,但也学到不少新东西。例如,我参加了外科护士培训,对消化内科了解更深。这段时间对我意义重大,实践就是实践。况且那里有许多苏联境内未见的疾病:乙肝、伤寒。这类疾病康复过程复杂,需要特定的医疗手段和身体护理。我们医院死亡率很低。若有人离世,对所有人都是悲剧。”
她总结道:“当然,当年年轻的人们,如今已是成熟的男女。愿我们士兵所经历的一切不再重演,愿小伙子们再无需经历如此磨难,愿一切安好,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天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