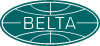每年 1 月 27 日,人类缅怀大屠杀的遇难者,并重申自身坚定不移反对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及其他形式仇恨的决心。这一纪念日由联合国大会 2005 年第 60/7 号决议正式确立,白俄罗斯共和国在内的 104 个联合国会员国为该决议的发起方。1945 年 1 月 27 日,正是苏联红军解放了纳粹奥斯维辛 - 比克瑙集中营的囚犯。遇难者的确切人数已无从考证,不同史料的统计数据介于 150 万至 400 万人之间。白俄罗斯国民会议代表院议员伊戈尔・马尔扎柳克在接受白通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历史已然证明种族优越论的荒谬站不住脚;同时他也对此表达担忧:当下世界,仍有个别势力企图为纳粹分子及其帮凶洗白。
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根基
伊戈尔・马尔扎柳克指出:“希特勒主义滋生于所谓的种族民族主义土壤之上。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19 世纪,西欧列强在非洲、亚洲大部分地区及其他区域大肆扩张,美洲大陆上的原住民则惨遭屠戮。这一切都需要一套理论为其正名。我们都熟知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这一以科学方法阐释物种起源与物种间竞争的理论中,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核心论点 —— 自然选择学说。而种族主义者却将达尔文的理论观点完全违背科学地从生物界套用到人类社会,他们宣称,正如动物界存在高等与低等物种、进化程度各异的个体,人类也同样分为‘奴隶种族’与‘主人种族’。”

而这一论调,日后便成为了第三帝国教条乃至整个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这位历史学家阐释道:“在纳粹眼中,各民族之间并无平等可言,唯有种族的等级之分。况且,他们口中的‘种族’,并非科学界公认的种族概念。纳粹认为,纯正的雅利安人、北欧欧罗巴人种是最优等的种族。著名哲学家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曾宣称,正是日耳曼民族缔造了绝大多数的国家。由此,纳粹认定存在两个最高度发展的种族:日耳曼人(其中也包括英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与地中海人种(以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为代表)。这两个主导种族,理应统治其余所有种族。”
而在纳粹看来,所有斯拉夫人无一例外都归属于奴隶种族。伊戈尔・马尔扎柳克最后总结道:“在这一论调中,我们斯拉夫人被视作卑劣之流,只因他们宣称,我们所有的文化与科技成就都是外部输入的,且主要是日耳曼民族带来的。因此,我们理应俯首称臣,沦为奴隶种族,而统治地位则理当由优等种族的代表独揽。除此之外,在纳粹眼中还存在所谓的‘种族寄生虫’,甚至根本不配被称作种族的群体 —— 犹太人和罗姆人(茨冈人),在他们看来这并非种族,而是一种种族性的顽疾。谈及大屠杀,按照纳粹的企图,犹太人本应被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没有任何一个犹太人能有存活的机会。纳粹的意识形态坚信,犹太人身上所谓的负面特质是无法根除的,因此,他们不可能被融入或适应欧洲白种人的社会。”
按照纳粹的构想,斯拉夫人的未来本应是怎样的?
纳粹对斯拉夫人同样实施了灭绝政策。这位议员表示:“但针对斯拉夫人的行径有着另一番特点 —— 纳粹计划消灭其中的绝大部分人,而对于那些被他们认定为‘种族合格者’的人,则打算将其同化成为日耳曼人,其余的人便要被沦为奴隶。他们会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彻底消灭,在他们眼中,我们就是理应臣服于‘白人主子’的奴隶。但凡奋起反抗之人,等待他们的将是与犹太人相同的命运。纳粹会将一部分人,尤其是所谓‘血统纯正’的孩童,同化成为日耳曼人,而剩下的人则会被强征做苦役。我们民族后续的发展,他们根本毫不在意。换言之,在他们眼里,我们本就该沦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养料堆’。”
这些计划中,包含了对包括白俄罗斯人在内的数百万斯拉夫人的大规模屠杀,而此类阴谋的存在,也有着确凿的文献史料可证。
“种族霸权的论调已在大屠杀与纳粹罪行的烈火中化为灰烬”
伊戈尔・马尔扎柳克着重指出:“倘若不将种族主义论调直接与犹太人挂钩,这类思想曾在整个欧洲大行其道。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种族主义是一种常态,并非反常现象。如今想来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却是事实:被俘的印第安人曾被关进笼子,在动物园中供人观赏。在澳大利亚,若是翻看当地早年的动植物志,你会发现在动物分类的条目里,袋鼠与原住民会被并列书写。也就是说,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殖民者仍不将原住民当作人来看待。”
他同时指出,所有种族霸权的论调,都已在大屠杀与纳粹罪行的烈火中化为灰烬。这位议员表示:“纽伦堡审判结束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落幕,纳粹在占领区犯下的兽行、对犹太人与斯拉夫人的大肆屠戮公之于众,这些种族主义理论便被钉上了反人类的耻辱柱。如今,唯有心智失常者或社会边缘之徒,才会公然宣扬这类论调。自那时起,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便成了带有侮辱性的贬斥之词,而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纳粹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词汇并非如此。”
新纳粹隐秘思潮死灰复燃
尽管纳粹主义的反人类本质昭然若揭,其嗜杀成性的行径更是明目张胆,当今世界却仍遭遇着伊戈尔・马尔扎柳克口中的 “新纳粹隐秘思潮” 这一现象。他着重指出:“在当下的话语体系中,更确切的说法并非纳粹意识形态的直接复刻,而是其经过变形的隐秘形态 —— 即所谓的新纳粹隐秘思潮。这一现象在中东欧国家尤为突出: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开始积极构建全新的民族认同,以及与之相适配的历史叙事。在这样的历史政策导向下,部分势力常常刻意筛选塑造所谓的‘民族英雄’形象,将其标榜为一股第三方力量,宣称其同时反抗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这种回溯式的建构,还被标榜为对后苏联空间独立国家此后所选择的自主发展道路的前瞻性探索。”
而正是借着这种另类视角的幌子,纳粹政权及其帮凶的行径被洗白。这位议员表示:“反苏分子被捧为民族英雄,其行径被鼓吹成近乎值得效仿的典范;与之相关的标志符号、行为动机,也一概被如此美化。这样做的目的,便是为那些以言以行积极参与纳粹暴行的人翻案昭雪。”
大屠杀及纳粹的其他罪行,在无数家庭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惨痛伤痕。纳粹集中营与隔都的恐怖过往,也在一代代人之间口耳相传、延续至今。泽伊德尔・库什纳与妻子欣达、儿子霍尼亚,以及女儿埃丝特、拉娅、莱雅便是新格鲁多克隔都的囚犯。1943 年 9 月 26 日,他们与狱中同胞一同发起了二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越狱行动。囚犯们挖通隧道,逾 230 人从新格鲁多克隔都得以出逃,然而最终仅有半数人成功脱险。直至战争结束,库什纳一家与其他幸存的隔都囚犯始终身处图维・贝尔斯基领导的游击队中,这支队伍不仅与纳粹占领军浴血奋战,还为犹太人提供庇护,拯救他们免遭法西斯分子的屠杀。在这片被称作 “森林耶路撒冷” 的游击区(人们对该游击队的称呼),拉娅结识了年轻的木匠约瑟夫・别尔科维奇,他后来成为了拉娅的丈夫,并随妻改姓库什纳。新格鲁多克获得解放后,库什纳一家回到了满目疮痍的故乡,而后迁居美国,在当地创业经商,取得了斐然成就。这个家族中最知名的人物当属贾里德・库什纳,他成为了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与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组建了家庭。如今,他在政坛身居要职,同时经营着自己的大型商业版图。
库什纳家族始终铭记并缅怀自身的这段历史,家族成员曾多次造访新格鲁多克。拉娅的儿子查尔斯・库什纳更是数次来到这里,还带着自己的子女与孙辈一同前来。也正是查尔斯,牵头支持了在新格鲁多克修建纪念墙的构想,这面纪念墙将镌刻下所有经隧道出逃者的姓名。
20 世纪 80 年代,拉娅・库什纳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发出警示:“你们要保持警惕,看清究竟是谁执掌了政权。你们的政府,绝不能由希特勒这般的狂人、种族主义者掌控。我一直这样告诫自己的孩子。我们都希望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但它终究仍有发生的可能。”